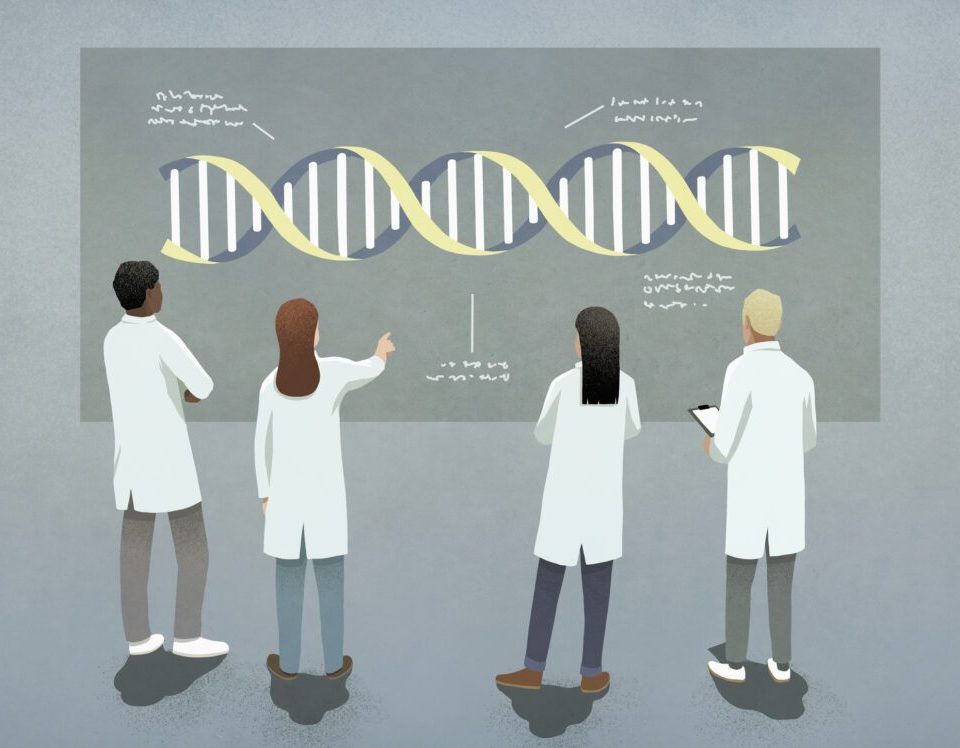創新社會治理視野下祠堂與教會的比較
2024年4月16日
父亲的饮食影响精子及其儿子的健康
2024年6月7日從鄉村宗族到城市宗族——當代宗族研究的新進展
文 | 週大鳴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教授、移民與族群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
摘要: 社經文化的發展,促成宗族形態發生不同程度的變遷。 從時間維度來看,宗族的類型可分為傳統宗族和現代宗族; 從空間緯度上看,宗族又可分為鄉村宗族和城市宗族。 檢視和研究不同形態宗族的變化發展歷程,可認識並掌握它們在特定的時空下是如何完成轉型的,及其對一方山水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影響。 為此,學界有必要加強對各種形態宗族的研究,尤其是城市宗族的研究。
關鍵字: 宗族制度; 鄉村宗族; 城市宗族; 文化轉型
文章來源:《思想戰線》2016 年第2 期,註釋從略。
費孝通先生提出「文化轉型」① 近年來成為學術界關注的重要概念。 我國隨著都市化進程的加速,從鄉村文明轉向城市文明已經不可逆轉。 根植於鄉村社會的宗族制度,無疑為文化轉型研究提供了一個切入點。 ② 本文從人類學的視角,綜合相關宗族研究的脈絡,來看宗族的轉型。 宗族,作為中國傳統社會的基本單元,具有相當全面的社會功能,構成整個社會結構的基礎。 而宗族組織及其規範,與儒家文化具有高度的、內在的、精神和邏輯的合一性,因此宗族及其相關問題便成為學術界研究中國社會的一個重要切入點。 ③ 韋伯在分析中國社會時,就把中國社會稱為「家族結構式的社會」。 葛學溥在《華南的鄉村生活》中,將「家族主義社會學」作為書中的副標題,認為家族主義是中國社會生活的特徵。 ④ 弗里德曼關於宗族的研究發表後,有的學者稱之為中國社會的「研究典範」。 ⑤
其實,中國人類學、社會學對宗族的關注由來已久。 林耀華在《義序的宗族研究》中,對一個單姓宗族村莊進行了結構—功能分析。 此後又在《金翼: 中國家族制度的社會學研究》中,透過建構單一家族的發展史,描繪了民國時期中國農村社會的圖景。 陳禮頌也對宗族進行過專門研究,根據自己在1934 年的調查資料撰寫了《1949 年前潮州宗族、村落、社區的研究》。 在陳達的《南洋華僑與閩粵社會》,費孝通的《江村經濟》,楊懋春的《一個中國村莊: 山東台頭》等著作中,宗族/家族則是作為社會文化的一個方面而被 加以考察。
許烺光從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的角度研究了中國宗族。 他在《宗族·種姓·俱樂部》中指出,中國人最重要的集團是宗族,宗族對中國文明的重要性在以往的學術著作和一般著作中受到了廣泛的承認。 在中國的大部分地區,宗族一旦形成,便成了指導其成員行為舉止的組織。 宗族對中國人是至關重要的,因為它代表了一種重要的、著名的生活方式。 ⑥ 而他的《祖蔭下》一書,則在祖先崇拜為中心的文化框架中探討了宗族/家族。
朗·奧爾加、胡先纓、莫頓·弗雷德、福武直、清水盛光、仁井田升等學者也都關注過中國宗族,分別出版了《中國的家庭與社會》《中國的一般宗族 及其功能》《中國社會組織》《中國農村社會結構》《支那家族的構造》《中國農村家族》等許多論著。 而在人類學的宗族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學者當推弗里德曼。 弗里德曼對非洲研究中形成的氏族模式和世系群理論加以藉用和改造,從功能主義的角度出發建立了適用於中國社會的宗族理論範式。 弗里德曼界定了世系群、高級世系群、氏族等概念,從靜態和動態兩方面考察了宗族的結構、功能及其內部的分化裂變規則,並討論了宗族與宗族、宗族與國家之間 的關係。 其著作《中國東南的宗族組織》和《中國的宗族與社會: 福建與廣東》可謂是中國宗族研究中的里程碑,並對其後裴達禮、華琛夫婦等學者的研究都產生重要影響。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前30 年裡,人類學對中國宗族的研究有所沉寂,這一階段的相關研究主要開展在台灣和香港。 裴達禮的《一個中國宗族村莊》、華琛的《移民與中國宗族》等都是這段時期的作品。 改革開放之後,隨著國內宗族活動逐漸復甦,宗族再次成為學者研究的焦點。 在近二、三十年來中國社會轉型的大背景之下,眾多的學者就宗族復興的原因,宗族與社會變遷,宗族的現代化,宗族與現代社會政治、經濟、文化之間關係,宗族的現代性 等內容展開了廣泛而深入的探討。 相關的論述大致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主題的探討。
一、
宗族的界定: 家族—宗族—聯宗
宗族是個頗有爭議的概念。 學者們從不同的角度對宗族做出了界定,或是對家族、宗族、聯宗等近義詞進行了區分。
有些學者對宗族的界定存在著很大的彈性,可以包含從( 小) 家族到( 大) 聯宗這一系列的組織。 林耀華曾提出「宗族為家族的伸展,同一祖先傳衍而來的子孫,稱為宗族」。 ① 這界定將「宗族」置於「家族」層面之上,它強調同一祖先,並沒有規定親緣的遠近。 許烺光認同林頓「宗族主要來自單系大家庭的擴張( 和)以血緣原理為基礎」這一觀點,認為宗族「是一種沿男系或女系血統直接從家庭延長了的組織」。 他提出宗族有名稱、外婚、單系共同祖先等15 個特徵,之後又提出與宗族相關的7 個特徵,② 給出了宗族的判定細則。 杜贊奇的界定也首先強調了同一祖先,同時也關注了共同財產和共同地域等因素: 「宗族…是由同一祖先繁衍下來的人群,通常由共同財產和婚喪慶吊聯繫在一起,並且居住於 同一村莊。 identity)的一群人之謂,實際上即是今日吾人所謂群體或團體。 ‘宗族’之稱不過是說明以父系繼嗣關係,即所謂’宗’所界定出來的群體。 明確地區分了宗族及其相關概念。 弗里德曼在研究中國宗族時,借用了非洲研究中氏族—世系群的分析架構。 在《中國東南的宗族組織》中,他注意到了宗族範圍的不確定性,但未對其進行細述。 ⑤ 在其後的《中國的宗族與社會》一書中,他區分了lineage 和clan,認為二者之間的差別在於是否有共同的祠堂和財產。 ⑥ 弗里德曼也認為,應區分中國研究中的clan 和lineage,提出區別二者的主要標準是真實的系譜關係。 ⑦ 裴達禮從血緣關係、財產等角度出發區分了大家庭、宗族、同宗和同姓等概念。 ⑧ 華琛則以明確的繼嗣關係、共同財產、共同祭祖儀式、共同政治利益和族內出生等5 個特徵界定了宗族,並分別對宗族( Lineage) 、高等宗族( Higher - order Lineage ) 、 氏族( Clan) 、同姓會( Surname Association) 等概念進行了詳細辨析。 ⑨
從前人的著述中可以見得,將宗族當做一種文化特質或一種社會組織形式,來研究宗族與社會、文化、個人之間的關係,以及宗族對於它們的意義時,學者們 往往只點明「宗族」的內涵,並不對其外延進行嚴格限定。 在研究宗族類型時,人們才會對家族、聯宗等形態進行辨析。 徐揚傑反對某些學者企圖區別家族和宗族這兩個詞的做法,認為這種區分既沒必要,也不可能。
馮爾康說: 「( 宗族、家族…) 這些名詞,在學術界理解不一,距離甚至很大,筆者不能、也不必要在書中作出討論,僅依照個人的理解來使用。」① 即使是提出「聯宗的結果不是形成一個新的宗族組織,而是形成一個…功能性地緣聯盟」的錢杭,也承認「人們一般不認為它在性質上與宗族有什麼重大的區別 ,無非是…形成一個新的大宗族而已」。 ②
在中國社會裡,家族—宗族—聯宗,其實是具有相同本質的一系列組織。 從內在精神上而言,這類組織的結合遵從父系繼嗣和祖先( 或血緣/姓氏) 認同的原則; 從外在表現上而言,它們有族譜、祠堂、祠產和共祭儀式之類的 特徵。 如何在家—房—家族—宗族—聯宗—非宗族這一系列連續遞增的組織之中劃分出「宗族」的區間呢? 正如莊孔韶所言,「有組織的、自組織的和無組織的宗族 都有其存在的地方適應性特徵”,③ 不同地域、不同規模的宗族有其各自的特徵,前人所提出的族產、譜系之類的判定標準顯然是缺乏普適性的。 對於「宗族」的區間問題,本文持主位研究的立場,認為: 從文化承載者所採用的標準出發———這是他們的文化、他們的組織———研究者應以當事人自己所承認的 「宗族」為基礎來進行判斷,而不宜生搬硬套客位研究中產生的標準而對其進行割裂研究。 由此,本文的「宗族」一詞包含了家族、聯宗這一類的組織,並不計較其規模大小、血緣關係是否真實等細節問題。
二、
現代宗族: 變遷、現況與趨勢
作為中國社會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宗族隨著社會文化整體的變遷而不斷發展變化。 關於現代宗族,學者們探討了宗族變遷( 主要是宗族傳統的延續、衰落或復興) 的原因、宗族及其組織活動的現代形式、宗族未來的發展趨勢、現代宗族研究的方法等話題,也表達 了他們對於宗族復甦的態度。 下面略舉幾例。
筆者在對廣東潮州鳳凰村進行回訪研究後發現,當地的社會制度,已經由葛學溥筆下的“家族主義制度”轉變成為家族與國家政治制度相結合的混合型製度。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一段時間裡,宗族制度曾經被打垮,而近年來族譜的重修和祭祖的恢復,又顯示了宗族意識的復興。 ④ 宗族在物質和精神兩個層面上滿足了漢人的需求,涵括了血統、認同、儀式、宗教、倫理和法律等多種要素的宗族理念,早已內化為漢民族精神的組成部分。 宗族可能會在酷烈的運動中被壓制得無聲無息,但絕不會被徹底摧毀,一旦環境許可,又會頑強地展現其生命力。 改革開放之後,國家政策的改變為宗族復興創造了製度環境,財富的增加使宗族復興有了經濟基礎,對外開放、華僑返鄉加速了復興的過程。 宗族能夠幫助推動國家和社會公共事務的運行,推動鄉村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不應對其進行迴避或一味的打擊,而應當與其溝通,並加以適當的引導和監督。 ⑤王銘銘對福建安溪美法村家族組織與社會過程進行了社區社會史的研究,考察了現代國家和政府在製度、政權和文化諸方面對這個兼有血緣和地緣的「家族鄉村」的改造。 他把家族社區與現代政治變遷相聯繫,以此解釋新的行政與文化力量對鄉土社會的影響,理解目前地方傳統的複雜處境,並透過對家族和社區的個案調查來窺視中國這個大社會, 力圖提供一個社區研究的新範例。 ⑥
王滬寧以歷史唯物論的立場,分析了村落家族文化的現況、特質、結構、功能、歷史發展與嬗變,以及這些內容的社會意義或與社會發展的關係,認為村落家族文化的存在具有 物質和精神雙重禀性,而物質生產力是其長期存在的首要理由,社會革命和政治革命對家族文化形成了強大衝擊,而經濟體制和生產力發展水平則能從根本上動搖家族文化的基礎。 目前的鄉村改革雖然形式上誘發了村落家族文化的恢復,但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資源總量的增長,最終將擴大消解村落家族文化的物質力量。 他不否認村落家族文化尚存在正面因素,但也明確地提出應該創造宏觀社會條件促進其消解。 ⑦
馮爾康整理了中國宗族由古至今的發展史,考察了現代宗親會的狀況,指出宗族具有適應性,能夠根據社會需要來調節其組織形式和內容,豐富和發展其功能,而宗族 生命力的一個重要來源是以血緣關係和祖先信仰為基礎的內在凝聚力。 現代宗族在組織管理、成員吸收、功能等方面都發生了演變,很難說它是否會存在於後現代社會,但至少在若干時間內,它會存在並不斷改變。 他提出,有些近現代宗族保留了傳統因素,基本上與明清時代一樣,沒能反映變化了的宗族時代特點,而有些宗族則與從前的宗族有了重大區別,主要表現在成員構成、組織 管理、宗族功能等方面。 ①
錢杭從宗族結構、譜牒、祠堂、宗族文化等方面考察了宗族的現代轉型,從心理基礎和製度環境兩方面探討了當代宗族復興的原因。 他認為,漢人宗族具有內在創新機制,當下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內容,可以用一種恰當的方式介入宗族觀念的更新與改造過程中,人們並不反對二者的結合,而是將對宗族傳統 的尊重納入依社會主義準則要求的整個生活方式。 ②
阮雲星對義序宗族進行了歷史人類學考察,發現這個昔日的「宗族鄉村」今日已不再是宗族「自治」的鄉村單位,而只是現代國家建設運動和鄉村製度下的非( 準 ) 制度性的“傳統姓氏地域”,義序鄉村的現實和變動是“變化”與“慣性”、“新”與“舊”諸因素交織、磨合的展現。 他也提出“結構轉換的宗族形態論”,主要從血緣/宗法與政治的關係的視角來解讀中國宗族及其結構變遷,認為20 世紀50 年代之後的“宗族”,已經是後制度性的、 主要存在於傳統文化中的“文化的宗族”,適用於“後制度性的’宗族’”分析框架,應與近代之前“制度性的宗族”進行區分研究。 ③
現代宗族,或曰現代“宗族”,與先前的宗族之間存在差異,這是得到一致認可的事實。 目前還沒有共識的是,現代宗族已經演化到何種程度? 甚或於,現代社會中被稱為「宗族」的事物/現像是否還是真正意義上的宗族? 它與傳統上的宗族之間是否存在 本質差異? 大部分學者在研究宗族的現狀和變遷過程時,並不質疑現代宗族的確然性。 還有一些學者則強調了現代「宗族」的異質性。 如科大衛、劉志偉等人認為,明清以後在華南地區發展起來的所謂“宗族”,並不是中國歷史上從來就有的製度,也不是所有中國人的社會共有的製度。 這種「宗族」不是一般人類學家所謂的“血緣群體”,其意識形態也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祖先及血脈的觀念,它的發展是國家政治變化和經濟發展的一種表現,是國家禮儀 改變並向地方社會滲透過程在時間和空間上的擴展。 ④ 錢杭曾申明,近年來重新恢復的宗族組織,應被看成是傳統宗族轉型過程中的這一階段產物,應該全部加上引號,以示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宗族在性質上的區別 。 ⑤ 阮雲星將古代宗族與近現代“宗族”相提並論時,也特意給“宗族”一詞加上了引號,將其稱為“民俗’宗族’”“文化的宗族”,並提出這種“後制度 性的’宗族’”,應該與清末以前“制度性的宗族”進行區別考察。 ⑥ 馮爾康在論述宗族的現代轉向時,曾提出家族「演化」與「異化」的兩種趨勢,認為應區分兩者之間的本質差異。 ⑦ 馮爾康後來沒有對此提議做進一步的探究,而事實上,他所做的這項劃分本身還頗待商榷。
由此又出現了一個問題,現代社會中的宗族或「宗族」 ( 引號之別) ,到底是新瓶裝舊酒呢,還是舊瓶裝新酒? 宗族只是在表現形式上發生了變化,但 仍然保持其內部深含的文化核心和文化心理? 或者,「宗族」所賴以存在的文化基礎及其本身的文化蘊意早已消失,留下的只是空有其形? 現代社會中,人們據 以判為是宗族或「宗族」的事項,如修譜、建祠、共同祭祖等,究竟是宗族傳統的核心內容,還是人們藉以舉行群體活動的「宗族」招牌? 面對這個排中的 命題,研究者必須做出選擇。
關於中國的宗族從古至今的發展過程,學者們提出了不同的分期方法,如李文治的“三期說”,徐揚傑的“四期說”,馮爾康的“五期說”等。 ⑧ 參照前人對中國宗族的分期,本文在此排出一個大致的宗族演化序列: 原始社會末期父系家長制—先秦君國宗族制—漢唐士族宗族制—宋元大官僚宗族制—明清紳衿 宗族制—近現代…宗族制( 現代宗族的普遍特徵目前還難以定論,因此暫且用省略號代替修飾語) 。 如果這個演化序列成立,那麼現代宗族就在漫長的宗族發展過程中取得了一席之地,關於「現代『宗族』」還是不是宗族的疑慮也就自然消解了。 就像社會文化的所有其他組成部分一樣,宗族也因時代而變遷,部分的嬗變並不影響其整體的延續性。 本文在假設前述序列成立的基礎上確定了研究立場,認為現在所呈現的宗族事項正是現代宗族的本質屬性,而其與先前宗族相異的部分則視作是無甚妨礙的外在形式。
三、農村宗族—城市宗族:研究中的區分與偏向
在中國,宗族制度普遍存在於各個時代和各個地域之中。 為了研究的方便,學者們從不同角度對宗族做出了區分。 如依成員的社會地位而劃分皇( 王) 族宗族、貴族宗族和平民宗族等,① 根據所屬民族的不同而劃分分漢族宗族、壯族宗族、瑤族宗族等,② 根據時代不同而劃分上古宗族、 中古宗族、近代宗族等,③ 依地域不同而劃分華北宗族、華南宗族、東南宗族等。 ④ 現代學者的中國宗族研究中,又出現了「農村宗族」和「城市宗族」的分野。
早在殷周「君統宗族制」時期,城市就已是君王貴族宗族活動的重要場所。 兩千多年來,中國城市中一直存在著宗族活動。 在對古代宗族的研究中幾乎不見對「城市宗族」和「鄉村宗族」的區分,而對近現代宗族的研究中出現的這一區分,不管是研究者有意識或無意識的行為,至少說明二者 之間出現了較大差異,也反映了現代宗族以及現代社會的特徵。 正如古代宗族之間和宗族內部明顯的等級性與中國古代社會中森嚴的等級制度相符合,現代宗族的「農村」和「城市」之分,或許正體現了現代中國社會中顯著的城鄉二元 化差異,顯示城鄉之間的巨大差別,是現代中國社會的特徵。 隨著城鄉一體化的推進和城鄉差異的縮小,「城市宗族」和「農村宗族」之間的差別或許也會逐漸淡化。 對於現代中國宗族的研究,國內外許多學者都趨向關注農村宗族。 許多論著中都赫然標有“農村宗族”或“鄉村宗族”等字眼,這表示此類研究的焦點乃是農村宗族; 許多論著雖然沒有明文寫出“農村宗族”,但從文中對“宗族” 的論述可以見得,作者仍然以農村社會作為研究的背景,或是把宗族與農村社會緊密連結在一起。 在「農村宗族」受到廣泛重視的同時,與之相對應的「城市宗族」卻不大引人注目。 從中國期刊全文資料庫的一項檢索結果中可以略見,與宗族相關研究中呈現的城鄉不平衡狀況。 以「標題」為檢索項,對1979 年至2009 年的入庫文獻進行精確檢索: 含「宗族」一詞的文獻有1 089 篇;含「宗族」並且「農村」的文獻有212 篇,含 「宗族」且「鄉村」的文獻有63 篇; 含「宗族」且「城市」的文獻有1 篇,含「宗族」且「都市」的文獻有1 篇。
研究現代宗族文化和宗族社會的學者們對「農村宗族」的側重,可以認為是城市社會與農村社會的不同特徵使然。 在城市社會中,以業緣、趣緣等為取向的人際關係日漸活躍,而以血緣、姻緣等為取向的人際關係卻趨於衰微。 城市的現代性、異質性和複雜性被凸顯出來,而家族、宗族等概念則容易被忽略。 相對而言,農村社會被認為是傳統的、同質性較高的,其結構較簡單,血緣、姻緣等關係濃厚。 以親屬關係為基礎的家族、宗族概念在農村社會中更容易受到重視。 另外,在20 世紀幾場深刻的社會政治變革中,城市宗族比農村宗族受到的衝擊更為劇烈,而宗族在農村的復甦卻比在城市更加迅速而廣泛。 與城市宗族研究相比,農村宗族研究更能獲得豐富而全面的材料。
除了上述在諸學科中普遍存在原因之外,人類學及其鄰近學科對農村宗族的“偏愛”,至少還受到其他兩個特殊因素的影響。 首先,人類學與生俱來的鄉土情結決定了農村宗族在中國人類學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作為「誕生於原住民社會研究」的學科,人類學的田野研究地點大多在遠離城市的鄉村地區,而作為中國社會文化的關鍵組成部分,宗族在鄉村社會研究中必須受到重視。 例如,第一個在中國進行田野調查的人類學者葛學溥就在他所製定的村落調查提綱中,把宗族作為「族群關係」和「社會組織」的中心內容加以強調,並在此次調查基礎上寫 就的常見於宗族史的分期研究,如馮爾康等將中國宗族分為先秦典型宗族、秦唐間世族、士族族、宋元間大官僚宗族等。 參見馮爾康《中國宗族史》,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 例如弗里德曼《中國東南的宗族組織》將其研究的宗族限定於「東南」地區,又如唐軍《伏與綿延-—當代華北村落家族的生長歷程》則是對「華北」地區村落 家族的研究。
《華南的鄉村生活》中提出,鳳凰村的社會系統只能被描述為家族主義。 研究中國鄉村社會的人類學者都需要關注農村宗族,因為要真正了解中國社會文化,就不可能繞過宗族這個主題。 第二,既有的農村宗族研究成果,引致了後來的學者對該領域的持續關注,可謂是學術研究中的「路徑依賴」。 後人在進行宗族相關研究時,容易受前人研究結論和研究範式的影響,而依循前人研究路線的結果,則是農村宗族研究的愈發興盛和城市宗族研究的愈發沉寂。 一個典型例子是,弗里德曼在對中國東南部鄉村宗族的研究中所創立的宗族研究範式: “之後的人類學者如……等都採用他的宗族概念,對他有所批評的中外學者 如…等人也…在此基礎上展開不同的陳述、批評與修正。
為了討論的方便,本文以國家行政區劃上的縣為界,將宗族分為“城市宗族”和“鄉村宗族”,主要在縣級以上城市的城區或其鄰近②範圍內開展活動的 宗族屬於“城市宗族”,主要在鄉鎮和村里開展活動的宗族屬於“鄉村宗族”( 文中經常出現的“農村宗族”一詞是對其他學者說法的沿用,其含義等同於“鄉村宗族”) 。 此分類可適用於國內大部分地區,但其在社會經濟非常發達地區的適用性,仍需另行討論。 時至今日,學者們已經對農村宗族進行了較為全面的研究,其探討的議題囊括了農村宗族復興的原因、農村宗族的功能、農村宗族的現代化、農村宗族與民主政治的關係、農村宗族與 社會經濟的關係等各方面。 關於現代農村宗族的研究成果早已是數不勝數,然而,關於城市宗族的研究卻稀少而零落,關注城市宗族研究的學者還為數不多。 筆者就曾指出,學術界對都市社群中的宗族關注度不夠,對城市裡的宗族關注度不夠。 ③ 為了彌補這一缺憾,筆者曾組織課題組對城市的宗族進行調查和研究,以了解都市化對宗族的影響亦即宗族在都市化過程中的變遷。 研究小組對梅州、廣州、深圳等地的城市宗族活動進行了研究,並出版了一系列論點。
四、城市宗族研究
弗里德曼、裴達禮等學者曾就城市宗族做過專門的研究。 如裴達禮在《傳統城市裡的大家族》一文中將家庭、宗族、同宗、同姓和支族之間的區別作為一個重要問題進行了探討,對宗族、同宗、同姓這幾種家族形式在城市中存在 的可能性進行了詳細分析,並以實例說明了城市內宗族和同宗的樣式,關注到了財產所有權或共有權、城鄉生活和經濟的差別、城市地理流動性和社會名流等因素對城市宗族活動的 作用。 在此例之外,還有一些學者對大城市中宗親會、族人活動一類的主題進行了研究。
如華琛對新界沙田文氏宗族的研究中包括了文氏宗族成員在國外城市中的活動。 在《移民與中國宗族》一書中,華琛考察了移民浪潮對文氏宗族村落的影響,敘述了村中宗族生活的變遷和宗族成員在倫敦生活和工作的狀況。 他發現,在周圍村落都逐漸「現代化」的同時,大量村民赴英工作卻使文氏村落保持了傳統形態,也使文氏宗族得到了強化。 書中的文氏宗族成員在外出時依靠宗族成員間的幫助,與老家保持著緊密的聯繫,但沒有在倫敦城中建立宗族組織。 該書雖然沒有研究城市中的宗族組織,但較為詳細地敘述了文氏宗族如何在族人分居大洋兩地的情形下得以維繫和發展,並從反面道出了城市中建立宗族組織的一個阻礙因素 : 人們對新的居處沒有歸宿感。 ④
在當今鄉村高速都市化的社會背景下,有些學者關注都市化過程對宗族變遷的影響並進行了相關的研究。 關於這個主題,目前研究得較多的是城中村宗族。 城中村宗族的由來,主要是在都市化過程中,原先的農村宗族整體、從動地轉變為城市宗族。 城市近郊的鄉村因市區的迅速擴張而被直接劃歸到城市範圍之內,不少人在一夜之間由“農民”變為“居民”。 人們的戶籍身分雖然可以在瞬間改變,但他們的生活方式和傳統習俗的改變卻不是一蹴而就。 村中原有的、由“農民”組成並管理的“農村宗族”,其內核延續下來,而外殼則變成了由“市民”組成並管理的“城市宗族”。 城中村宗族由農村宗族直接轉變而來,與原先的農村宗族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同時又因其所處環境和成員身份的轉變而具有了城市生活的特徵。
孫慶忠、高崇等在學術名村廣州南景的追蹤研究中,都將都市化進程中原村落宗族的變遷作為調查的重點內容。 孫慶忠選取廣州市三個城中村( 南景、下渡和舊鳳凰) 為調查點,研究了三種類型的都市村民宗族生活形態,考察了宗族在城市中的存在狀態、運作機制、維持的動因 以及演進趨勢。 他提出,都市村民的宗族生活在從鄉村聚落到都市村莊的演進中一直存活的原因是中國社會儒家傳統延續的結果,是村民對生存環境適應的需要,更是經濟利益的內在要求。 在逐漸融入都市街區、受控於城市管理體制的背景下,城中村宗族組織展現了獨特個性特徵,也面臨宗族權力再度萎縮和宗族意識日益消解的困境。 都市宗族的最終消逝是歷史的必然,但傳統鄉民的文化模式依然會在形式化的宗族生活中由淺及淡地延續。 ①
周建新曾關注廣東梅州一個城中村( 鐘村) 宗族的都市化遭遇。 在《動盪的圍龍屋》一書中,闡述了宗族成員為保護祖傳宗祠免受拆除危險而發起護祠運動的原因、過程、特徵及其文化意義,採用「過程—事件分析」的研究 路徑與「文化抗爭中相互建構」的分析框架,深入分析了宗族社會與現代變遷、文化保護與現代化等議題,探討了行動背後的心理活動、行為方式及策略手段。 他認為,鐘村宗族由於護祠文化抗爭而得以復興和重建,宗族觀念加強,宗族意識顯性化,具體表現為成立宗族組織、集體祭祖、宗親間聯繫增強、開展宗族歷史文化研究和 其他宗族性活動等。 在事件中的宗族,不僅是製度化的、文化形式的,也是建構出來的。 重構的宗族與傳統意義上、日常生活中的宗族有較大不同,宗族內部是非同質的,帶有個人的慾望和特徵。 城中村宗族是現代較常見的一種城市宗族,它們往往屬於宗族範疇內的家族類型。 此外,在縣級區域中,也不乏另一種聯宗類型的宗族組織。 聯宗合族的活動自古已有,而且一般是發生在城市之中,如康熙年間始建的「鄧氏廣州大宗祠」。 ② 瀨川昌久認為,「有清一代,縣城已成為設置…… ‘上位世系群’總部宗祠的場所」。 ③ 對於這種聯宗型宗族活動的考察,也屬於城市宗族研究的一部分。
劉道超曾對廣西博白縣黃峭山公祠籌建過程進行了個案研究,意在剖析當代背景下宗族的實質及其對族群關係與建構和諧社會的影響。 他在《當代宗族與國家關係之思考———廣西博白縣黃峭山公祠籌建個案調查》一文中,記述了籌建事件的緣起和經過、宗祠籌委會的管理體制和工作作風,分析 了宗祠籌委會成員的特質、標語口號與祠堂楹聯,表述了自己對宗祠復興事件的理解與觀點,並向政府決策者提出了參考建議。 他贊成陳國才、馮爾康等人的觀點,認為在當前經濟發展程度不高、社會保障制度和法規仍不健全,人們安全和歸屬感缺失的情形下,宗族意識會被人們想起並加以運用,但宗族 在社會文化方面的功能已經大不如前,而宗族依從於政權的狀況未曾改變。 ④
筆者組隊對深圳龍崗的風東社區的宗族組織進行過調查,調查結論表明,風東宗族在城市化背景下發生了一系列變化。 這表現在: 宗族族田與祖產的消失,以及社區經濟方式的改變,使宗族與經濟利益之間關係發生了變化,宗族集體活動的經濟來源發生了改變; 城市化帶來的雜居、社會福利 的新變化,在現階段還沒有完全改變宗族聚居的方式; 宗族的權威體系發生了變化,一方面族長與實際管理者發生了分離,動搖了年齡序列的權威地位,另一方面,宗族管理者 與居民小組管理者發生部分重合,調和了非正式權力與正式權力之間的關係; 宗族認同由「族際區分」的功能逐漸延伸到「他我區分」的功能,宗族認同向地域認同轉化; 最後宗族習俗在都市背景下有大量適應性調整。 筆者認為,都市化雖然帶來了社會變遷,使宗族最早存在的基礎受到衝擊,但宗族並沒有與那些傳統的生存方式共存亡。 相反,伴隨著都市化,宗族已經慢慢透過適應性調整,以新的形式存在於現代都市社會中。 ⑤最後要指出「重視宗族的研究,分析宗族制度的基礎特徵及其現代轉化,已是刻不容緩的事情!」⑥ 宗族組織及其活動在村級—鄉級—縣級—市級遞變的生活 區域中有著不同的形態和特徵。 若要更全面地了解現代宗族的各種形態及其特徵,就必須對各種類型的鄉村宗族或城市宗族進行分別的考察和綜合的比較。 而在當今城市宗族研究相對稀少的情況下,就更應該加強對包括城中村宗族、城市宗親會等不同類型在內的城市宗族的研究。